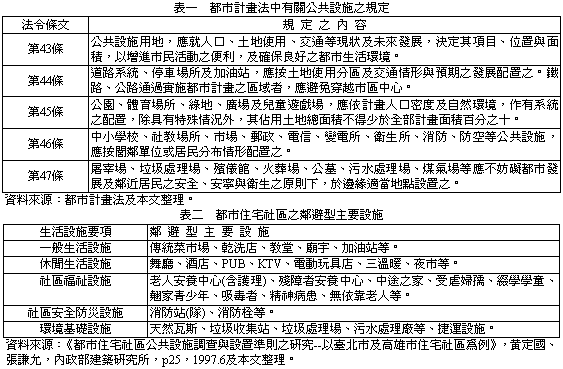∼以都會區捷運系統為例 (上)
☆ 林茂成 ☆
關鍵詞:鄰避型設施、區位選擇、處理模式、都會區、捷運系統。
|
壹、緒論 公共設施是為了提供都市或社區居民在運輸、教育、醫療、衛生等各方面所需要的公共建設。因此公共設施乃屬於一種福利性設施,提供居民生活上的需求、便利居民生活、確保居住和環境品質。但過去台灣所發生的社會運動,多有因公共設施的設置所引起。不僅包括鄰避效果較高的設施設置,如焚化廠、垃圾處理廠、捷運機廠、變電站、通風口及路線高架經過或地下穿越等,也包括了鄰避效果低的設施設置,如公園、學校、棒球場、捷運車站、出入口等。公共設施既為都市內必要的服務性設施,提供居民生活上之便利與舒適,但卻仍有遭致民眾反對設置的現象產生,值得進一步省思。隨著政治解嚴,台灣社會與民眾開始對各項議題賦予更多的關注,進而促使台灣環境面臨轉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所帶來的各項環境議題,以及永續發展理念的日受重視,漸為台灣環境規劃注入新思維,而也愈來愈多的人主張民眾應該廣泛且直接地參與到影響其區域生態、生活、生產環境的任何規劃、設計、與開發行為或過程,也就是說民眾應該被賦予權利參加重要決策的行為或過程。 因此,本文以國內社會運動或環保抗爭歷史較為陌生但確已默默在民眾慢慢地覺查到生活環境受到影響的都會區捷運系統之鄰避設施區位選擇思維,從過去歷史之環保社會運動脈絡與捷運實際發生之案例探討,研擬如何透過階段性檢核、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規劃協調模式與經由行政資源系統的組織運作,思考如何將上下與雙方的意見進行整合,以期在公共設施設置的各個環結中,能掌握可能產生衝突的因子與探討較佳之處理模式,俾將衝突所產生的成本降至最低,進而提出些新看法與建議,以供後續作業改善之參考。貳、文獻回顧與相關理論 一、文獻回顧 (一)鄰避設施之居民認知與環境態度所謂鄰避設施是指地方上所不願意接受的設施,但是卻是達成社會公共福利所不可或缺的,但因該設施會對附近居民產生實質或潛在負面的影響,諸如:空氣污染、噪音或房價下滑,所以十分容易造成附近居民喊出「不要在我家後院」(Not in my back yard)與「地方上不想要的土地使用」(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的口號,進而強烈反對該設施設在其住家附近。然而何以民眾會有強烈的抗爭行動?政府在整個興建過程中又有哪些問題?以及如何降低民眾的鄰避現象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9]。在李永展教授與林啟賢先生於「鄰避型公共設施之環境態度與更新接受意願之研究--以臺北市為例」[6]所做之研究結果發現,大多數受訪民眾對鄰避型的公共設施態度具持平的看法,而不少受訪民眾則顯示了某種程度的「鄰避情結」。而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受訪民眾不同意「政府已經提供了足夠的公共設施相關風險資訊」的說法,這些受訪民眾明白地表達了他們對政府在處理鄰避型公共設施設置或更新問題時無法扮演足夠的角色之關切。其經由因子分析的操作,由受訪民眾的環境態度中歸納出心理、社會公平、政治決策、動機與行動等五個因子,其中以心理因子、社會公平因子與動機因子最為受訪民眾重視。 (二)鄰避設施衝突之談判支援與管理分析 在台灣社會趨於多元化、民主化的過程中,居民、開發商與政府之間的衝突逐漸浮上檯面;而隨著民眾對環境意識的逐漸覺醒,許多都市計畫負面性設施及鄰避設施的設置經常受到爭議,導致政府、規劃者與民眾之間容易發生衝突,而在眾多處理衝突的方式當中,談判是獲各界一致推崇的解決之道。而在探討都市計畫談判中的支援與管理時,理論上應先對都市計畫中衝突與談判歷程有所分析,掌握談判支援方向的需求,然後再融合衝突解決與談判理論的輔佐,搭配適當的系統發展方法,以確定整個支援體系的架構[8]。「鄰避」Not-In-My-Back-Yard, NIMBY)往往被視為是個人或社區反對某種設施或土地使用所表現出來的態度,這種又被稱為鄰避症候群(NIMBY Syndrome)的環境衝突,在世界各國已經成為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因此,在整體規劃鄰避設施時便應重視鄰避衝突之管理,以消弭設施周圍民眾的不滿,進而減緩鄰避設施設置、更新、營運的阻力。民眾反對鄰避設施的原因可歸納為經濟、社會、心理及政治等四個層面,而鄰避衝突產生的原因至少包含空間認知不同,利益分配不均、資源分配不均、資訊傳播不正確等因素。為消弭都市服務設施的鄰避效果,應透過合作管理的策略,採用鄰避設施的衝突管理模式,以協調並消弭各種不必要的鄰避衝突。而為有效管理鄰避設施的空間衝突,李永展教授在「鄰避設施衝突管理之研究」[5]曾提出風險減輕方案、經濟誘因及民眾參與等三種政策工具。然而此種公共財設置的目的在於服務鄰里或維持經濟與社會文化的發展,但並非所有的公共財都受到人民的歡迎,此種財貨即為嫌惡性公共財。嫌惡性公共財設置之所以遭遇到民眾的抗拒(resist),主因是其所產生的利益由全社會所共享,但其所造成的的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卻由當地居民承擔,此種配置難免有失公允。所以在處理嫌惡性公共財問題時必須格外謹慎,以期能兼顧社會的發展與公平。為消弭反對聲浪並符合社會之公平與正義,適當的提供補償誘因策略(compensative incentives)是必要的,且此亦能提高居民接受度,增加設置的可能。通常嫌惡性公共財(Public Goods with NIMBY)的最終地點,總是呈現出一種「環境的種族主義」(environmental racism)或「環境階級主義」(environmental classism),因為具有嫌惡性的公共財最終地點經常是落於較落後或是政治勢力較薄弱的地區。也由於嫌惡性公共財會對社區的利益(benefit)或損害(damage)產生分配效果(distribution effect),如何使所產生的衝擊公平分配(equity),是選址(location)所考慮的主要向度[11]。 (三)公共設施設置之環境衝突管理 公共設施是為了提供都市或社區居民在運輸、教育、醫療、衛生等各方面所需要的公共建設。因此公共設施乃屬於一種福利性設施,提供居民生活上的需求、便利居民生活、確保居住和環境品質,同時防止災害的發生並確保居民的安全。惟反觀過去台灣所發生的社會運動,多有因公共設施的設置所引起。不僅包括鄰避效果較高的設施設置,如焚化廠、垃圾處理廠等,也包括了鄰避效果低的設施設置,如公園、學校、棒球場等。公共設施既為都市內必要的服務性設施,提供居民生活上之便利與舒適,但卻仍有遭致民眾反對設置的現象產生,值得進一步省思。因此建立一套預防衝突產生的機制,透過階段性檢核、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規劃協調模式,經由里長系統、社區發展協會、社區規劃師三個行政資源系統,透過組織的運作,將上下雙方的意見進行整合,以期在公共設施設置的各個環結中,能掌握可能產生衝突的因子,將衝突所產生的成本降至最低[4]。 (四)都市公共設施鄰避效果與計畫空間公平性 所謂都市服務設施係指「提供社會、文化、經濟、政治與宗教等服務機能之都市設施」。但由於都市服務設施的種類與使用性質的不同,對都市環境或生活品質也產生不同的影響,有些對環境有正面的「迎毗」效果(YIMBY,Yes-In-My-Back-Yard)(Lake,1993),有些卻會產生負面的「鄰避」效果(NIMBY,Not-In-My-Back-Yard,不要再我家後院)(李永展,1994a;曾明遜,1994a;Groothuis & Miller,1994;Lake,1993), 而有些則是迎毗效果與鄰避效果同時存在。回顧相關研究,在界定迎毗效果與鄰避效果時多過於主觀,因而對有鄰避效果之設施的探討有所缺漏之遺憾,因此宜從居民的接受意願來界定鄰避效果,不事先設定那些設施是迎毗設施或鄰避設施,以符合「由下而上」的規劃理念。為免居民所認知的鄰避效果會因都市階層而有差異及造成差異,宜從環境行為的角度予以釐清,以找出影響都市服務設施鄰避的因子,以建立都市服務設施鄰避效果之概念模式,同時研擬減輕都市服務設施鄰避效果的對策,以提供都市服務設施規劃、配置的參考[16]。公共設施計畫乃為維護都市生活環境品質,提供生活必須之設施,滿足都市居民生活所需服務。因此對於資源分配之空間公平性,應予以重視與達成,然而空間公平之概念難以操作與落實,因此以往規劃師進行資源配置時總是忽略此一議題。故如何建立一套公共設施計畫之空間公平性評估方法是重要的課題。雖然近年來已有不少研究對於公共資源分配的公平性進行探討,然而其衡量方式總是透過非空間性的總體經濟指標進行公平性分析,而缺乏考量較小尺度之空間可能存在之不公平。此種分析基礎存在著諸如:分析單位的不適切、未能考量空間阻隔所產生之效用損耗、分析角度僅由單一觀點而未能由不同設施間所呈現之整體效用之公平性觀點進行評估等缺陷。故若能以空間分析方法為基礎,並結合地理資訊系統之空間資料分析、處理與視覺展繪,應可建立公共設施空間公平性之評估方法[3]。 (五)永續環境規劃之省思 台灣環境問題與危機是建構在其特殊的政治脈絡與經濟政策(李永展,1996),自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後,在政治上採取高壓統治,在經濟上加速土地改革的結果,不僅造就了壓迫式成長下的台灣經濟奇蹟,更杜絕了台灣人民關心環境自發性的意識;因此,經濟奇蹟的代價即是土地資源及生態環境的耗竭,工業文明的線性邏輯思考成為時代價值取向與遊戲規則。但隨著政治解嚴,台灣社會與民眾開始對各項議題賦予更多的關注,進而促使台灣環境面臨轉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所帶來的各項環境議題與省思,以及永續發展理念的日受重視,漸為台灣環境規劃注入新思維,而也愈來愈多的人主張民眾應該廣泛且直接地參與到影響其生態、生活、生產環境的任何規劃、設計、與開發行為或過程,也就是說民眾應該「被賦予權利」參加重要決策的行為或過程,這個主張可以從台灣各地活絡的社區活動得到驗證(例如社區總體營造,李永展1998b、1997a)。賦權(empowerment)(或參與)可定義為「讓共享許多重要價值的所有人能面對面進行互動」(Sanoff, 1990:i)[21],它是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面向,就此而言,賦權是由參與者對某個決策的控制,因此,賦權牽涉到基本體制及架構的改變,它隱含了對決策施與相當程度的影響力[11]。 二、相關法令規定 (一)區域及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區域計畫法乃為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之保育利用,人口及產業活動之合理分布,以加速並健全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利;其中非都市土地依其使用區之性質,編定為甲種建築、乙種建築、丙種建築、丁種建築、農牧、林業、養殖、鹽業、礦業、窯業、交通、水利、遊憩、古蹟保存、生態保護、國土保安、墳墓、特定目的事業等用地。而都市計畫法旨在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並促進市、鎮、鄉街有計畫之均衡發展,都市計畫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樂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而言。在都市計畫法中,有關公共設施規定之相關條文為43-47條,其內容摘要歸納如表一。 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Zoning control)是將都市境內的土地適當地劃分區域,規定各個區域的使用;換言之,即是以合理的規定都市分區,指導其分區使用,以限制私有的土地及土地上建築物的不合理發展,使都市成為一個良好的居住環境及更為有效率的工作所在;因此各級政府依據都市計畫法完成施行細則及制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其中與都市住宅社區有關之鄰避設施彙整如表二。
依土地法第二百零八條「國家因左列公共事業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規定徵收私有土地。…」大眾捷運法第六條「大眾捷運系統需用之土地,得依法徵收或撥用之。」大眾捷運法第七條「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方發展,地方主管機關得自行開發或與私人、團體聯合開發大眾捷運系統場、站與路線之土地及毗鄰地區之土地。」,按前節之相關鄰避設施理論及台北捷運之相關規劃手冊、規範與實際案例中,都會區捷運系統之鄰避效果較高的設施有捷運路線(以地面、高架及穿越民房之地下段為最)通風豎井及冷卻水塔位置、主變電站(Bulk Supply Substation, 簡稱”BSS”)牽引動力變電站(Traction Substation, 簡稱”TSS”)與捷運機廠等,及鄰避效果較低之捷運站體位置、地面車站與高架車站之月台型式、出入口設施設置等。 三、區位選擇理論 公共設施設置的目的在於服務鄰里或維持經濟與社會文化的發展,但並非所有的公共設施都會受到人民的歡迎,此種設施即為「嫌惡性公共設施」或稱為「鄰避型設施」。鄰避型設施之所以遭遇到民眾的抗拒(resist),主因是其所產生的利益由全社會所共享,但其所造成的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卻由當地居民承擔,此種配置難免有失公允。所以在處理鄰避型設施問題時必須格外謹慎,以期能兼顧社會的發展與公平。為消弭反對聲浪並符合社會之公平與正義,適當的提供補償誘因策略(compensative incentives)是必要的,且此亦能提高居民接受度,增加設置的可能。 從過去資料統計與歷史之案例顯示鄰避型設施的通常最終地點,總是會呈現出一種「環境的種族主義」(environmental racism)或「環境階級主義」(environmental classism)[11],因為具有嫌惡性的鄰避型設施最終地點經常是落於較落後或是政治勢力較薄弱的地區。也由於鄰避型設施會對社區的利益(benefit)或損害(damage)產生分配效果(distribution effect),因此如何使所產生的衝擊公平分配(equity),是選址(location)所考慮的主要向度。陳彥樺先生在其碩士論文中[11]曾以經濟學的角度出發,配合經濟學的理論與工具,分析嫌惡性公共財的設置情形與居民之決策過程。其中包含外部性模型、賽局模型及遷移模型,從負外部性來看,嫌惡性公共財設置相當於是將污染全數移轉的概念。可移轉外部性(shiftable externality)的課稅情形是對設置社區需給予適當的補償,而所需補償金將來自於其它地區,為對稱之價格策略。若以移轉投入之多寡決定設置地點,則都市化、商業化程度較高者中選的可能性較低。其次是導入賽局理論的基本模型之中,分析嫌惡性公共財的設置問題,顯現其特性及各社區之決策過程,甚而是各種均衡結果(equilibrium and outcome)。結果發現:1.當社區數目越多設置的可能性越低;2.於設施有效使用範圍內僅會有一嫌惡性公共財產生;3.設置於該地所產生負外部性越小的社區設置的可能性越大。此研究所得與其他領域之研究結果一致;接著其以議價賽局決定補償金之數額時,發現當其他社區所認定嫌惡性公共財的損害大於設置地區認定的損害時,議價才會有結果。此外信息的不同亦會影響成交的可能性,當為完全信息時之成交價格將會小於不完全信息之價格,此時可能交易的範圍較大。最後其再以賽局之擴展式(extensive form)探討設置時可能的抗爭情形,發現只要居民認為有利可圖,如可能遷走或更多補償金,則會有抗爭發生;此外,政府的態度亦是居民是否抗爭的主要因素,發現政府越是風險趨避或越重視抗爭所造成的形象損害,則越可能受到居民的威脅,也越可能同意補償。 而在嫌惡性公共財設置之後,其負外部性特徵透過遷移(migration)過程,則會影響人口配置問題;若以政策面介入,則需對嫌惡性公共財的設置地區提供更多的非嫌惡性公共財,而使該地區之寧適性得以提昇;此外其研究結果認為亦可減少其稅賦負擔,若政策可行亦可提高對其之補償金,如此能使各地區更均衡發展,使地方公共財的提供與人口配置達到最適境界(optimal)。參、鄰避型設施規劃之經驗與未來發展趨勢 一、鄰避型設施之居民抗爭背景因素 (一)鄰比情節的問題從公共政策的理論而言,社會民眾對於公權力的挑戰與質疑,造成許多公共建設的窒礙難行,其中最難以處理的設施為「鄰比情節」(Not-In-My-Backyard,簡稱為NIMBY)議題;根據維斯(Vittes,et al., 1993)[12]及其同僚的看法,所謂鄰比情節是指「不要在我家後院」的主張意指:(1)鄰比情節是一種全面性地拒絕被認為有害於生存權與環境權的公共設施之態度;(2)鄰比態度基本上是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的主張,它強調以環境價值衡量是否興建公共設施的標準;(3)鄰比態度的發展不須有任何技術面、經濟面的或行政面的理論知識,它的重點是一項情緒性的反應。由此看來,鄰比情節可以說是公共政策制定與執行上相當難以突破的瓶頸,並不是「說理」就可以解決的問題糾葛[12],如捷運出入口設置之居民異議「我要方便,但不要設在我家門口」原由即是。 (二)回饋的法制化與合理化問題 目前我國公共政策普遍遭遇到此種困境,以台電及中油公司為例,其每年所編列的睦鄰經費幾乎占整個國營事業睦鄰經費的九成以上,但問題並未真的解決;因此沒想到原則的退讓,讓民眾食髓知味,此種效應所引發的場面就很難收拾了。此外,目前環保回饋尚未完全法制化,主要問題的癥結有:(1)回饋基金直接撥付到鄉鎮市區公所,鄉鎮市區長基於政治(選舉或派系)考慮,往往以「有福大家享」的方式讓鄰避設施周邊地區居民分享該回饋基金,造成那些距離鄰避設施最近、受害程度最為嚴重的居民之反彈。因此,如何貫徹回饋的精神:「受益付費,受害補償」,並且貫徹以「受害程度」或「距離遠近」為分配回饋基金的標準,將是促使「合理化」的主要課題。(2)回饋的金額與項目雖然林林總總,但民眾似乎並未感受到回饋的益處,對於小金額的回饋活動,如廟會、社區或其他活動,民眾抱怨連連,認為金額太少;對於大金額的回饋活動,如修橋舖路、興建圖書館等,民眾認為那本來是鄉鎮市區公所就應該做的事與回饋無關。因此,如何簡化回饋項目,落實回饋精神,從而發揮回饋的效果,將是未來應該認真面對的問題[12],而捷運設施之補償雖已依「大眾捷運系統路線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惟其餘鄰避設施之社會課題項目,仍僅援相關規定辦理。 (三)鄰避危害因果關係的鑑定問題 在自力救濟中,最頭疼的問題是如何證明損害行為與污染事實之間的因果關係;特別是當損害事實尚未發生,僅具可能性或預測性的損害,而民眾基於保障生命與財產的理由,向設施擁有者提種種的要求。究應如何尋求科學証據,以鑑定公害因果之關係,尺寸拿捏,頗屬不易。過去發生的自力救濟事件,民眾似乎比較信任學術機構進行科學證據調查的公信力;不過仍不少民眾對於學術機構所頒布的不利之調查結果,往往不願接受,也造成鑑定機構的困擾。因此,如何建立權威性的公害因果關係鑑定機構,將是未來應該注意的課題[12]。 (四)信任危機問題 民主政治常軌下,自力救濟的發生與處理,民眾應該信任並且服從公權力的行使,不過實際情形是民眾對地方政府普遍持著不信任的態度,一般民眾也往往無法接受政府官員對公害原因所鑑定出來的不利結果;因此,政府與人民之間產生了「信任差距」(Credibility Gap)。從公共政策而言,政府機構的政策行動與命令,無法得到人民順從;受害民眾沒有意願遵行政策制定的遊戲規則,這是發生了正當性危機(Legitimacy Crisis);政策制定體系的正當性是政策能夠推行的關鍵因素[12],如捷運路線之必須穿越居民土地房屋之分析決策模式,迭有居民不論透過民意代表或自救會方式抗爭,即是很好的例子。 (五)自力救濟處理過程的泛政治化問題 就民主國家的發展而言,壓力政治(Pressure Politices)雖是民主政治之常軌;不過,壓力政治的運作仍有明確的遊戲規則;就我國政府機關處理自力救濟的情形而論,民意代表介入行政決策過程,為民眾關說某項請求,本不足為奇;惟如果關說事項不合理或違法,甚至涉及金錢利益的索取或利用政治勢力作秀,則這種關說壓力對於行政決策便容易產生負面的作用與處理的困難[12]。 (六)資訊遭受扭曲與無法有效傳遞的問題 社區民眾對於鄰避資訊的吸收出現了兩大問題:第一、資訊遭受嚴重扭曲,不正確的資訊經過口口相傳,傳遞到每位民眾腦海中,很難加以改正;第二、由於社區民眾的環保教育知識不夠,阻礙了資訊的吸收,太過僵化的文宣方式,往往無法有效地傳達到每位民眾腦海中。因此,每逢發生糾紛衝突,民眾往往以訛傳訛的方式傳達錯誤的訊息,這對於設施擁有者或執行者的傷害是很大的。因此,今天很多鄰避設施所面臨的新挑戰,並不是資訊不足的問題,而是資訊太過充分,但卻嚴重被扭曲或無法順利傳達的問題[12]。 一、鄰避型設施居民抗爭之因應策略 任何鄰避型設施之居民抗爭的形成,任一政策利害關係人自然無法逃避責任,一昧地相互指責對方的不是,只能加深問題的裂痕,惟有在整合不同政策利害關係人的多元利益觀點下,有效的政策方案才能順利產生;因此,丘昌泰教授在「環保抗爭的因應策略」[12]中提供了以下許多省思空間與建設性之看法,值得吾人在從事計劃研擬、方案規劃與實務技術操作之參考。(一)重視「過程的公開」更甚於重視「結果的公布」 任何鄰避設施的醞釀或興建過程,本身就是一種良好的環境教育機會,主辦機關必須設法讓社區民眾知道規劃興建過程是公開的,沒有任何不可以公開的秘密,讓民眾知道該等設施的必要性、意義、限制與功能,以加強民眾對於該設施的認同感。換言之,我們千萬不要以為設施規劃興建的完成就代表任務的結束,事實上過程中的教育更為重要,必須賦予社區民眾知的權力。 (二)多一些「誠意溝通」,少一些「圍堵沉默」 許多鄰避型設施糾紛問題之發生,皆由於彼此的溝通不夠,欠缺相互諒解對方立場與態度的機會。事實上,在一向講求人情的台灣社會中,彼此建立溝通管道,樹立溝通誠意,是可以化解許多阻力的。因此,主辦機關應經常與當地民眾進行不同形態的政策溝通,以瞭解彼此的想法。事實上,民眾參與環境管制可能成為極有價值的社會資源,如果能善加引導,不但可減輕糾紛對社會所造成的衝擊,更能促使環境公益的實現。為達此目標,未來應設法在行政程序上,拓展民眾參與對話的機會,而過去完全排除居民參與決策的作法,確有檢討的必要。 (三)用民眾可以瞭解的普通語言,宣導所設立之鄰避型設施,使之通俗化 以捷運車站出入口及通風豎井為例,可在充分瞭解當地居民結構背景下,採用其能接受的文宣方式(如漫畫等),淺易地傳達該等設施係為提供乘客進出車站便利乘客在捷運系統與其他交通工具之轉乘的必要構造物,以及提供設備通風換氣之必要通風口,而傳達該等設施之配置,在造型上、量體上、環境衝擊上、質感上,是如何地考量到居民之安全、健康,及其如何與環境相融合與區域文化特質相呼喚的具體做法,而確能提昇鄰避設施周圍的環境品質等;簡易的傳達方式,可使民眾能夠真正體認到設施的效能,以展現出溝通的誠意。 (四)協調處理機制之定位 在鄰避設施無法取得更有利的區位時,居民抗爭的實體,應透過法定的鑑定機構,以進一步釐清事實真相或責任歸屬、受影響程度、對象與範圍大小。民眾並不是毫無理性,他們要求的是:「確定污染、受害來源,明確公害之責任」,如果公害原因遲遲無法定案,糾紛就容易走上暴力之途;因此,如何成立具公信力的、機動性的法定鑑定小組,為當務之急。此外,公害賠償亦是另一根本的問題,也是許多抗議民眾之主要訴求,然而目前大都以協調或私下和解的方式達成,並無有關公害賠償(補償)之相關法令來配合;因此,過去民眾漫天要價,業者拒絕退讓,主辦機關拖延處理,顯然均是欠缺明顯的規範,乃是糾紛擴大的主因。 <未完待續> |